作者:【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 胡宪
D27 我激怒了一头母象

我毕竟是心里放不下事的人,早上睡不着,从日记本上撕张纸,给鲍勃写了封信。
“亲爱的鲍勃,我没有生气,只是为你难过。每一个人都应我诚挚的请求,骄傲地用母语写下了那句话,除了你。你玷污的自己祖国的文字,受辱的不是我。你曾说,你走出来是为了看不同于美国的世界,那么我想告诉你,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永远总是个笑话。(the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re not always a joke)”
车开动后,我趁大家不注意,假装到车前扔垃圾把信交到鲍勃手中。他一整天都再也没有说话。
今天去火山口,一路荒郊野岭不见人烟,倒有几次沙尘暴像龙卷风似地在天地间盘旋,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老天爷也好像在阴晴之间拿不定主意了,真不禁夸!
下午3点多钟,我们到了恩格罗恩格罗(Ngrongron)火山口国家公园。这里本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由于禁止农耕的政策给火山口里的马赛人造成生活困难,所以在1959年被划了出来,成为一个可以农耕的特殊保护区。
公园入口处有个另收费的小型展览,试图揭示人类如何从这里发源。似乎没人感兴趣,我们都坐在石阶上等小戴购票。塞治从“厕所”回来说坡上有大象,我和斯提娜大喜,沿着一条石板小路蜿蜒向上,走不远果然看见一头重约2吨的大象在林间吃树。我俩轻轻靠过去,15米左右伏下身“咔嚓、咔嚓”照了几张像。

大象斜眼睛瞅我们,掀了下耳朵,我们知道这是大象在警告我们不要靠近。本来我们也不敢再靠近,但以为保持距离看看总是可以的。没想到,大象马上又竖起了耳朵,而且这次是面向了我们。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斯提娜喊了一声:“shit!There is a baby over there。Run !”(屎!有一头小象在那儿呢,快跑!)我这时也看见了,可不是?就在这象妈妈的身后还跟着头小象,我们正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俩吓得扭头想跑,可是已然晚了。那头母象怒吼着,挺起长鼻向我们冲了过来。

山林震动,大地乱颤,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死神就这么近在眼前,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短跑速度能拿世界冠军!
也幸亏是下坡,我觉得自己根本是在飞。斯提娜一边跑一边大叫,我一边跑一边痛悔:难道今日就要为好奇心和自由散漫付出生命代价吗?
在此危急关头,乔治带着几个人冲了上来。虽然从他们的眼里,我知道身后并没有大象,但仍然不敢回头。
大象的吼声经久不衰,像是怒气难消。我和斯提娜臊眉耷眼地回来了,毫无“凯旋”之耀。没人出声责备我们,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次冒险完全没有必要,甚至非常愚蠢。我已经拍了上百张大象照片了,这次母象的突然发飙说不定就是我的长焦镜头惹的祸。从一开始向导就告诉我们:大象第一次扇耳朵是说:不许靠近;第二次扇耳朵是说:你必须后退;这时,你就一定要后退,莫等它第三次掀耳;但是,带着幼崽的母象不可以此常规而论,一定要远避。哼,我们还傻不啦叽的等它第二次扇耳呢!

进园后,车继续爬坡,再然后,就在火山唇上行驶了。我很喜欢这个“唇”字。“火山口”,“火山唇”,有口有唇的,多么人性化的描述!
今晚在火山唇营——“Simba”(辛巴,“狮王”的名字)露宿。这是一片不到200平方米的开阔地,中间一棵大树地标似的拔地而起,显得异常雄伟繁茂;三面丛林,没有围栏;离我们约20米,两头凶巴巴的野牛“牛视眈眈”地注视着走来走去的人。一种感觉,一种身为人类的感觉,只有在这种极端环境中才能被强烈地体会和珍惜,而在人与人摩肩接踵的城市倒常常被忘记或惘然。
到达营地时,已有几个团队了,帐篷紧挨着帐篷,车辆紧挨着帐群,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距离也格外地近。很明显,在这里人们只有相互靠拢才能对动物产生一定的威慑力。小戴又重申了一遍纪律:要围火扎寨,天黑后只能帐边“如厕”。其实,不用他说我也不敢往远走,这营区给我的感觉是在山脊之上,无挡无拦的,抬脚多迈几步就可能掉到“爪哇国”去。

我去找厕所,迎面遇见一头收翅直立的大鸟,比我还高,尖嘴圆目,白领黑羽,像个穿礼服的绅士。看来它一点也不怕人,只是大概没见过我这种颜色的人,所以盯着我看却没有让路的意思。我举起长筒相机,它才有所顾忌地向一旁慢慢踱步,见我紧追不舍,加快步伐跑了几下,然后振翅飞去,扬起一片风尘。
厕所又脏又臭,门不能锁,好在分男分女。这一路我已经掌握营盘如厕习俗了。晚上好办,里面有光(不管是什么光)就是有人;白天若是门关着,就有讲究了:门外的人要先发出一声“牙”?(一定要二声),里边若是有人就要答一声“讶”!(一定要四声)
此时我不怕别的,就是担心这么薄的木板棚,哪里经得住野牛一拱,鬣狗一扑呢?为了不起夜,只有严格控制睡前进食进水。

大家帮忙准备晚餐,我看见鲍勃冻得直打哆嗦。这里海拔2000多米,气温只有几度,每个人都“捂”装起来,我穿了两件毛衣,可他只有一件外套。我上车在行李里翻出一件羊绒衫递给他,说;“我先生的,纯毛。”他犹豫了一下,默默接过去穿上了。
这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酒吧,只有呼啸的山风和野兽,大家各回各家。小戴说车是斜的,没法睡冰柜上,就在行李柜之间铺了垫子先躺下了。我往前挪了一排也铺床睡了。似乎没过多久就听到锅碗瓢盆有动静,我和小戴翻身起来,打开窗,手电光下,一只鬣狗一晃不见了。小戴说它不会走远,还会回来,让我别管,尽管去睡,反正吃的东西都收拾妥当了。我这时才发现本来说要睡在外边的乔治正睡在冰柜一侧,这么说现在是三个人睡在车里了。
车外就没有安静过,但考虑到他俩都太劳累,我收起了好奇心。又睡了不知多久,忽然大铁锅发出一阵巨响,车也摇晃了一下,小戴叫一声“不好”,窜了过来,接过我的强力电筒向车下照去。光柱内我只见一团漆黑,小戴却惊吼起来:“bush pig! Bush pig!”(丛林野猪)我这才看清眼前黑乎乎的是一头比饭桌还大、还高的巨兽正拿屁股对着我们,埋头吃我们今晚剩的,压在重型铁锅内准备明天再吃的意大利粉。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见过这么大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关窗,别让它扭头咬我一口。小戴用手电筒敲着车帮,“奥吃”、“奥吃”地轰赶。它磨蹭了半天才肯动窝,可这一下轮到我叫了,因为我眼看它直奔伊万娜和卡门的帐篷冲了过去。
这后果哪堪设想?此时远近又有几束手电筒光照射过来,混杂着人的吼声。那庞然大物好像是到了跟前才发现有障碍物,在离帐篷不到一米的地方猛地拐了个弯跑走了。小戴惊魂未定地用手电来回照,我们看到那条鬣狗还在车的另一侧伺机行动。
乔治始终一动不动,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又躺了下去,为今夜的际遇感慨万分:我,一个来自东方的黄皮肤女人,此时此刻躺在亿万年的火山之巅;头顶有野猪偷食,脚下有鬣狗侧目,身边还有一黑一白两个非洲男人一左一右地打着轻鼾……不和谐中透着和谐,和谐中又含了多少的不和谐。

———————— END ————————
广告

点击华人会广告图片可下载华人会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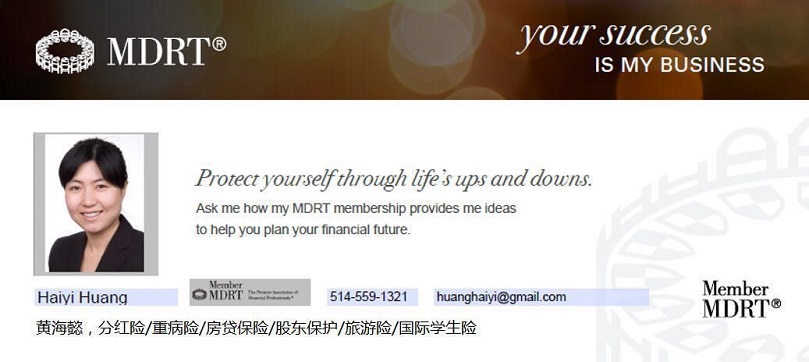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欢迎关注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网站

欢迎关注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微信公众号
欢迎惠顾广告!
联系电话:胡宪 514-246-3958,胡海 010-15901065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