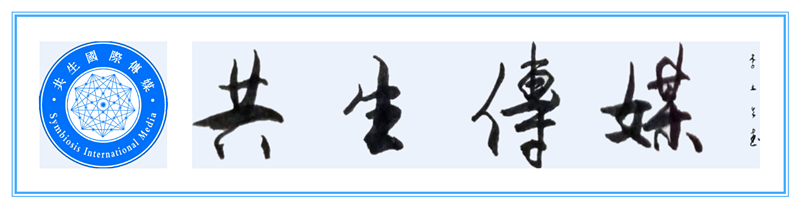
D11,赞比西河遇险

清晨把船推进桃红色的赞比西河一定可以镇痛,人人都说肌肉疼,但人人都疼到笑。因为出发早,河水清清,微风煦煦,划了没多会儿,就再没人说话了,谁都不忍破坏了这份静,这份宁。
忽然,前方依稀传来女人的歌声,待船靠近我们看到,原来有几个妇女正在河中洗澡。一个用花布遮住了下身的大婶看来刚刚洗完,笑着向我们挥手,唱歌的是个年轻姑娘,水面上只露出后仰的头和宽宽的肩膀。一圈“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半壁栅栏是用稀疏的树杆围成的,好像只为告诉河马人类在此“圈养”。
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歌声停顿,相反,看我们都望着她,那姑娘唱的更欢,甚至还将好大的黑脚丫抬出水面,随着歌的节奏,一起一落,溅起水花,啪啪作响,踢向我们。她眯着眼,快乐地咧着大嘴,瘦削的脸上突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几乎雪白到耳朵;她那样子自信且俏皮,让我联想起法国的“红磨坊”。不过,磨坊那种“大腿舞”哪里有眼前的“土风”来得大气?因为这黑女人的舞台可是天之下,她舞动的也不是浅薄的超短裙,而是威猛的赞比西。
能欣赏到这种舞蹈是一种福气。就像那个小女孩儿,看见有人失去脚,再不抱怨鞋子难看一样,我想我再也没有理由不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高高兴兴的了。
十点多钟我们靠边“water break”。我右脚蹬上岸,左脚刚离船,不等重心移过,忽然右脚下泥土一松,我整个人掉进水里。先以为岸边的水不会太深,哪想到水没了胸口脚还没沾底。我反应也算快的了,忙伸手够岸,明明扒到了,可那大块的泥土却随着我的下沉而塌落。
“这岸是空的!”我心知不妙,做着最坏打算。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小戴大叫一声“宪!”惊恐地合身扑倒岸边,在我没颈的最后一秒钟拉住了我的手。一米89的他将我湿淋淋地提了上来。
可能是被凉水激着了,憋了两天的我急于入厕。我扛着铁锹在20只眼睛的目送下,假装“没事儿人一个”,走向稀稀拉拉的灌木后。这铁锹很有讲究,它是上非洲“野厕”的特制工具。三角形的木柄头上横出一柄,用来挂手纸,柄头中有槽,用来装火柴。来之前,我准备了一块大方巾以便“蹲坑儿”时围腰,结果完全没有用上。因为我们并非行走在寸草不生的沙漠,男生可以一转身完事儿的这点事儿,我们女的只能用最快的速度钻进树丛。10次中有9次我的长发或衣裤会被挂住,好多次我都不得不扯断头发先脱身,回来后再要伙伴帮我摘除脑袋上的荆棘,难怪非洲女人都不留长发。

我走到纪律规定的10米处回头瞧去,不行!每个人的眉毛还是一真二切的。又走出几米,发现脚下有一堆象粪很新鲜。这说明大象刚刚走过,按说不会很快回来。不管这想法对不对,反正壮了自个儿的胆儿。拐了个弯儿,果然看不见大伙儿了,我按丛林规矩先用铁锹挖坑,可地太硬,恐怕是被大象踩实的。我拿脚使劲蹬锹也只能铲下一层表土。后来实在不能也不敢拖延时间了,我匆匆完毕,正要点火烧手纸,一声炸雷般的象吼吓得我两腿一软,几乎瘫下。我强自镇静,不回头,不四处瞅,想着克里斯说的话:“No paper is allowed in jungle!”(丛林不许有手纸留下)公德意识战胜了恐惧,我哆哆嗦嗦地擦了好几根火柴,才将手纸烧成灰烬。又哆嗦着铲了浮土埋脏灭迹,才又哆嗦着往回跑。迎头碰上前来寻我的克里斯,他埋怨了我几句,忽然把我拉到河边,跪在地上,撩起河水洗我的裤子。原来上衣差不多干了,但裤腿上还满是泥浆。我很难为情,也很感动。
午饭后,克里斯坐到我身边,指着远处的河马问我中文怎么说。我教他说“河——马。”他发音一步到位。我因材施教,进一步告诉他“河”与“马”的意思,并鼓励他说:“你看,你一下子就学到了三个中国词语:河,马,河马。”他兴奋得眼睛放光,接着问大象、犀牛、斑马的读音,认认真真地模仿。见一个“黢黑”的外国人对我母国文字这般有诚意,我高兴地牺牲掉午睡,连教了他10几个中国字,并简述了中国文字的形成史,例如“中国”两字为何这样写,日字、月字、目字、田字、男字等等的来由。
小戴也没有睡午觉,一直在旁认真听着,不知他心里是拿自己当陪读生还是偷艺者。

下午接着划船。大家的警惕性渐渐松懈,还时不时趁克里斯不注意拿出相机。我也照了几张。但我犯纪律是“小的溜”的:见物见景,快速掏出怀内袖珍数码,“咔嚓”一下后,立马掖回。可鲍勃一照起来就没完,我见他总不划,我也不划了,扭头看他拍照。仅仅几分钟,我们的船就与船队拉开了约50米的距离。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就在这次,我听到队友们一片尖叫,转过头一看:天哪!一头装甲车规模的河马(当然是公的)正好下水,将我们与大队切断了。
平常有人宠着时我胆子很小,怕这怕那,大呼小叫的,而一旦真正凶险来临,我却往往能立即调整自己,坦然面对。例如以前那两场大病,例如大峡谷几度危机,还有乘狗拉雪橇时险些送命……这次也不例外,我注视着河马沉声请示:“船长,我们该怎么办?” 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美加联军”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有希望化险为夷。可是身后没有一点声音,而我们的船却顺风向河马漂去。我一边倒浆定船,一边又连叫两声“captain”(船长)。没有反应,我改叫“鲍勃”,还是没人理,我回头一看,见鲍勃圆睁双目,嘴唇微张,面无血色,整个人像瞬间冻僵。这时,领队克里斯大喊:“别过来!绕大圈!”我猛一打浆,将船90度转向,拿出吃奶的力气向斜后方划去。
河马看不见了,连泡沫都没有了。但这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危险更大了。因为没有走远的河马可能潜伏在任何水域,却多疑地认为是我们挡住了它的去路。我放慢了速度,凭直觉猜判河马此时的位置。我先是与“它”平行,慢慢划向对岸,再沿着河边越过“它”向大队靠拢。我希望河马懂得我的心意:我对你心存敬畏,决不敢冒犯,请放过了我们吧!
鲍勃后来也划了,但他始终没说出一句话。我心说:难怪美国兵在越南会打败仗。
我和鲍勃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是自己的错,有什么话好讲?
晚上天阴,星星稀落,不见月影,围着篝火,我与克里斯、戴瑞克,这一黑一白两个非洲人聊天,渐渐谈话的内容越来越严肃,变成了政治讨论,论题涉及了种族,同性恋,非洲的文化和与世界的差距等等,最后不知怎的还讲到了我自己的移民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