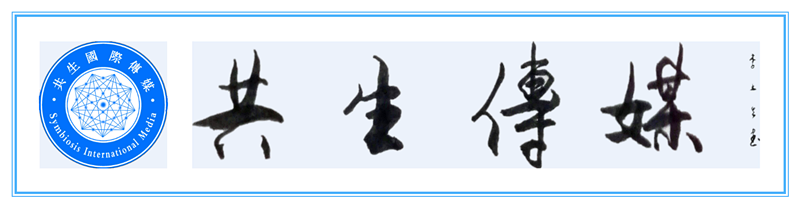
D10,赞比西河泛舟

自从每顿晚饭必须服上一粒“疟痢药”后,总是早早就犯困,到了凌晨2、3点钟又会因头疼醒来而再难入睡。预防疟疾的口服药有两种,一种是每周一粒,吃四周到五周,价钱略微便宜,但副作用大,让大夫一说“轻者发恶梦,重者患癫痫”,我根本不予考虑。另一种一天一粒,连吃38天,无甚副作用,最多有人出现头疼(就让我赶上了)。难是难在必须定时,前后误差仨小时以上就有风险:吃密了能中毒,吃疏了不管用,药量设计得分毫不差。大夫推荐时讲得很简单:“每天跟晚饭一起吃就不会忘了。”可他就没想到,我们这种旅游,吃饭是没有定点的。何况我这个人稀里马虎的,吃药根本是撞大运,今天5点,明天兴许就10点。我早想好了,不求药管用,就求带菌的蚊子嘴下开恩。
今明两天的活动是——“泛舟赞比西,露宿无人岛”。听上去多浪漫多写意呀!然而恰恰相反,这两天将是我们非洲之旅最艰苦、最危险的两天,也将是对我们的心力、体力、勇气和韧性,乃至人格的综合挑战和考验。

赞比西河,非洲第四大河,以河马之家闻名于世。河马,身长可达5米,重可接近4吨。这河里到底有多少河马,至今说不清楚。当地人认为平均每1平方米就有一头河马。河马看上去五短三粗、慵懒笨拙的,谁能想到它竟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呢?

斯提娜说(我还没查到资料)她看过书中统计,非洲人死于河马的人数要多于疾病。我问导游克里斯是否属实,他说:“我不是每天都听说有人生病,但我每天都听说有人被河马咬死或咬伤。我昨天刚去医院看我的表弟,他捞鱼时被河马袭击,幸亏水性好,拼命游上了岸,但左半边臂膀算是完了。”
这就是我们将要“泛舟”的河。

我们每人得到了一个一尺来高的塑料桶,用来装水、睡袋、三天的衣服和个人认为非带不可的物件。下水前,克里斯先教大家如何用桨,然后用极其严肃的语气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安全。他说:河马非食肉动物,你若不把它逼急了,它不会进攻人类。但问题是,它总错误地判断情势,以为自己面临威胁了而先下口为强。 我们的船队必须永远呈一列纵队前进,绝不能并排。对河马来讲,如果它见到左边是人类,右边还是人类,那就是战争了,它会不由分说地掀船咬人以求逃命。另外,不管是看到河马,还是其他动物,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岸上,谁都不许照相,因为你拿起相机的时候,就是置同船人生命于不顾的时候;第三天我会安排专门的快艇带大家游河拍照。

第二,合作。船,是双人单桨的独木舟。前后两个人的桨必须同边同时同方向用力,必须精诚合作,绝不允许偷奸耍滑。他比划着说:“你如果累了,就说累了,但若是这样摆动桨装样子,对我们非洲人,那就是‘fuck you!(操)’就是背叛,就是侮辱!”

我们9名队员加司机戴瑞克被克里斯分成5组,他带队。当他说出美国和加拿大联盟时,我和鲍勃不约而同地显出了失望。我知道他是想跟性感的卡门搭伙儿,而我则希望与人高马大的路易或小戴同舟。我说:“鲍勃,你真没运气。不过我会努力。”
我俩将各自的圆筒安置在船中央特制的洞里,又将帐篷和折叠椅塞进座位下,套上了救生马甲。按强弱搭配的原则,我算弱的,坐前边当“马达”,而小鼻子小眼儿、还没我个儿高的鲍勃倒成了我的船长(captain)。

我虽然臂力弱,但划船是我长项,小学、中学、大学都敢跟男生叫板。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傻呵呵地光轮胳膊,我是前俯后仰脚蹬,全身使劲。下水实习还没几分钟,人人都看出我有功底,加上我是唯一配有专业手套和鞋子的,就有人喊了:“宪,你以前也干过这个?”那天我说起在美国玩过“白浪漂流”,有人不服气地将信将疑。即使想低调,也得实话实说呗。我说:“独木舟只干过一次,但双桨小船打小就划。”
“你不是北京城里的人吗?”有人问。
“是啊,可北京城里有公园,公园里面有湖泊,湖泊里面有游船,我小学过队日,大学考完试,通常荡浆以庆。”我平心静气地回答。对中国的孤陋寡闻并不是他们的错。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正是每一个华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可不是唱高调。
鲍勃大乐,一个劲儿地叫:“宪!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可是这么一来,我就经常能感到是自己一人在划船了,特别是当周围出现了动物的时候。我还不能说什么,因为按规定条例:“马达”的功能就是只管不停地划桨,而船长则有权利根据是否离前船太近(2至3米)而决定自己划还是不划。这个小美国鬼子,真让他占到了便宜。
我小心眼地揣度鲍勃是不愿让大家看见他偷懒,才故意让我们的船总落在最后的。有几次我明明抓住机会超到了前边,结果又被他拖了后腿。位置在前的好处是看动物多,因为许多鸟呀,鹿呀什么的都怕羞,见人多就溜了,等我们这第六只船开到,往往只能瞅个尾巴。
什么叫没运气?碰到这种人就叫没运气! 唉,为了你将来有运气,你还别跟他真“运”气。
毕竟今非昔比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到体力不支,特别是有病的右臂和肩背都像在受酷刑,心脏也隐隐作痛。骄阳似火,“马甲”如棉,我汗流不止,几次几乎虚脱。我咬紧牙关,为了我的自我挑战计划,为了我所代表的两个国家,为了我自己的荣誉……天哪!——也为了活命,划吧您呢!
不是夸张,正当我在划与不划之间犹豫时,前船的小戴忽然冲着我们大:“Hippo! Hippo!”(河马)我随着他的手指扭头,果然,就在鲍勃身后2米远,一只圆圆的河马眼像潜水艇的潜望镜一样紧紧跟着我们的小船,小戴一边叫一边逃,鲍勃连回头瞧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他后来说以为我们在开玩笑)。此时此刻我划动着我的桨,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玩儿——命”。

太阳最毒的时候我们靠岸午餐,午休。克里斯有令:不得走出10米以外“入厕”。我自作聪明地跟小戴商量:“这么多天了,每次‘water-break’(放水)我都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来个‘男左女右,’以避免‘撞车’的尴尬呢?”小戴头也不抬地说:“我们非洲人不在乎这个,我们男女可以挨着拉屎聊天。”我讨了个没趣。听一个纯种白人口口声声称“我们非洲人”如何如何,总觉有点怪异。不过再想想,我也真是多事,怎么把世俗之气带到非洲来了呢?怎么就忘了在n年以前,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黄人,统统是光着屁股离开这片土地的,如今穿着衣服回来了,难道就以为可以指手画脚了吗?
把带气孔的大沿牛仔帽往脸上一扣,一为遮太阳,二为接鸟屎,找个斜坡儿躺下,居然睡着了。
我是疼醒的。全身四分五裂地疼。想到还有一天半,不由在“火炉子”里打了个寒颤。
两小时后,船队再度出发。鲍勃忽然问我:“你弱吗(are you weak),宪?”我没有掉头,回答:“我体质较弱,但意志很强。”几秒钟沉默后,鲍勃轻声说:“我也是”。 我们开始聊天。他说由于个头小,小时候常被人欺负,很多男子运动他都是靠意志力完成。至此我才知道,鲍勃已经32岁了(我一直以为他20浪荡岁),出身于美国北部某州的农耕家庭,信仰极端宗教,是11个孩子中老五,职业是教堂设计师,去年离了婚,很受打击,请长假旅行,目的地是非洲和东南亚。
“美国人都应该出来走走,”他说;“我本来以为美国为世界做了那么多贡献,美国人一定处处受欢迎。但出来两个月了,我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有的场合我必须考虑要不要说自己是美国人。”鲍勃是民主党员,911后,他投了布什的票,现在有些后悔。
河马越来越多,大片大片的褐红色在水面上沉浮,远看像小岛。为躲它们,我们的船荡过来,荡过去,河风强劲,更增加划船的难度,挪威人和“夫妻档”险象环生。
克里斯告诉我们,成年雄性河马,包括河马“爸爸”和河马“哥哥”们是不跟“家人”住在一起的,总是独往独来,而我们看到的一大家、一大家不动窝的河马群都是“妈妈”们和孩子们。河马的领域观念和家庭观念非常重,因此雄性河马之间常常爆发“失地之耻”和“夺妻之恨”的战争。克里斯能听出河马的吼声是呼唤,还是警告;是挑衅,还是哀伤。

还好,只划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就到了今晚的宿营地——荒凉的“象骨岛”。顾名思义,此岛因大象尸骨多而得名。我怀疑这里是老年大象自毙的地方,怕有忌讳,没敢问克里斯。小戴说他上次带队,亲见`12头大象从营地穿过。

克里斯重申了“野营”的危险性以及不准远离帐篷“放水”的纪律,然后大家协力卸船,把船掀翻扣在岸上,就一个挨着一个地安营扎寨了。有人开着玩笑:“我半夜会在你的帐篷外撒尿,嘻嘻……”
我在汉娜诚恳的邀请下同意与她们一起住。我们仨很快搭好了帐篷,她俩就迫不及待地趴到浅水区降温了。

图说:我们的帐篷
河水静静地流,一头大象在对岸悠闲地啃树,落日将我们的帐篷,男人蜕皮的背,还有一张张混合着快乐、警戒与疲倦的脸庞都染成了美丽的金色。我想将这里的一切都收入镜头。

处处是象粪,时时闻象吼。这名符其实的“野——营”历险让我们没时间疲劳,个个如惊弓之鸟。晚饭后,我们仰靠在河边,看萤火虫在灌木丛中飞舞着拉开夜幕,看星星陆续睁开亮晶晶的眼睛,笼罩孤岛的恐惧被一扫而光。

星空实在太美了,美得让人窒息,美得无可言状,美得所有人只能说出一句废话:“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星。”那满天的星星呀,多得像整个宇宙都在天堂集会,多的连银河都被星海淹没。
望着星空我胡思乱想,脑中忽然浮现一幅场景:若干天后,我回到了人儿、狗儿、猫儿的世界,我问人儿:“你看见过天吗?”然后在人儿迷惘的眼神中笑着跑开……那人儿一定当我有病吧?
我见过一张摄影师的作品:浓墨般漆黑的背景,一圈圈金色的光环,老师说那金圈是星星,是曝光一小时拍下的星星的轨迹。于是,我在折叠桌上支起“迷你”三脚架,对准了“维纳斯”(金星)试拍星星。我没有定时器,只能手动操作,从30秒曝光起步,不行,60秒,120秒,最后到了3分钟,星星们在我小小的相机屏幕上,终于长出了可爱的小尾巴,像金色的蝌蚪嬉戏于黑色的海洋。
“我拍到了星星!我拍到了星星!”我兴奋地告诉人们。
我虽然没能拍出那金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笨拙的手验证了地球的运转。这哪里是星星的轨迹啊,这分明是我生命的轨迹,它印证着我此生与天地之间不解的缘分,它印证着我今夜无价的童心。
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今夜满月,掰着手指头盼,像是小时候盼过年。虽然每一个人都在抱怨肌肉酸痛,但没有一个人舍得去睡。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着月神的降临。克里斯说;“宪,听说你会讲故事,来一个。”我讲了牛郎和织女,然后月亮就被我的故事引来了。

我们的对岸是丛林,丛林的上端先是泛起一抹红晕,这红晕越升越高,越升越大,越升越圆,原来这是月神娘娘醉红了的脸。她似刚刚出浴,纤尘不染;她像今夜主宰,俯视万物傲然升殿。她只随意丢了一个媚眼,我们就被宠得目瞪口呆;她仅将裙脚在河中轻抹了一下,赞比西就激动得红浪轻颤。
都说,月亮是被动的,她不会自己发光,所以总是苍白着脸。但在这非洲之夜,我不相信,我偏要说月亮和太阳是双胞胎!不信,那就看看我的照片:到底是月升还是日升根本就无法分辨。

以前只在倪匡的科幻小说中读过红色的月亮,那月亮导致全镇的人都疯了。我捧着相机里的红月亮着急地问怎么能让人相信我拍摄的是月亮而不是太阳?赛治看了一眼后说:“别担心,你把‘Mars’也照进来了。”果然,在月亮的左上角有一个亮点,那正是好心闯入镜头为我作证的火星!
谁说上帝不眷顾非洲?他给了非洲最辉煌的夜色。

图说:火星为我作证
——————— END ————————
广告

点击华人会广告图片可下载华人会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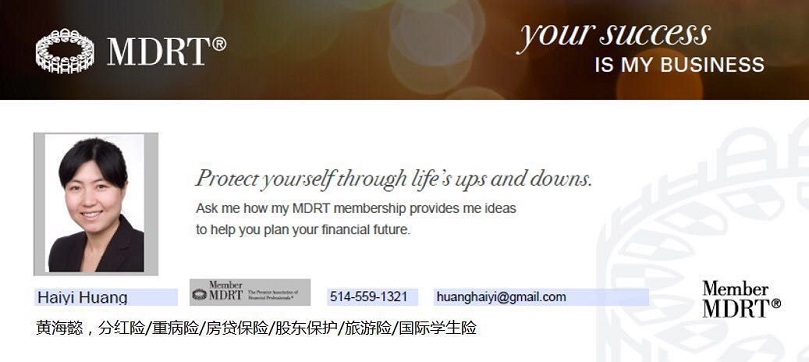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欢迎关注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网站

欢迎关注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微信公众号
欢迎惠顾广告!
联系电话:胡宪 514-246-3958,胡海 010-15901065716